“有时仅仅是一首诗,我们就找回了对世界的初恋。”
——题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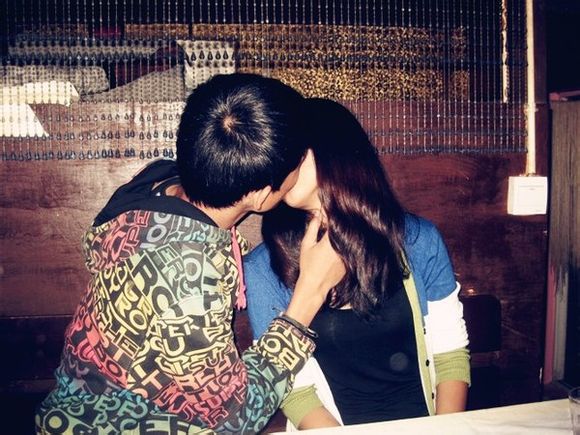
诗歌一直都是阐释学着迷的对象,因为它兼具神谕与谎言的双重特征,而诗人素来也兼具神使与骗子这两种名声。
在长长的诗的时光史中,我唯爱西方的诗歌。那些诗歌对我来说,既非神谕,亦非谎言,而是从生活切片中映出的一朵花,一片叶,一束光,一滴血。坐在自己喜欢的绿植旁,阳光浅浅地亲吻着书角,回响出一串串笑声与哭声,手边茶杯里逸出的清香伴奏着诗人们的私语,苏缨曾说过那像一个时代的低吟。
喜欢英国诗人奥登,喜欢他关于宿命与爱的独特见解。奥登曾写下诗句“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”,但在他深思熟虑后,又改为“我们必须相爱而且死亡。”从对爱的笃定到宣示爱与死是同一宿命的不同两面,从要么爱要么死,到除了爱,别无选择。这些诗句总像一阵微风轻轻吹过心房,一阵兵荒马乱。
偶尔看到他写的一篇墓志铭,虽然他仅写了一个人平凡的生平梗概,但在当时可适用于千万位死者。“他自由吗?他幸福吗?这个问题太可笑了:如果真有什么错了,我们当然知道。”它让我想到少年时张扬的幻想到成年也无非是这样的,我们到底有几分自我,怎样才能找回我们原本笑容里的真?生活,除了风中飞舞着的尘埃,我们还触摸到了什么呢?
我喜欢沉浸在甜蜜的悲哀里,在爱的完满与爱的缺憾中落泪,而最爱的是《葬礼蓝调》:“我以为爱可以永远,但我错了。不再需要星星了,把它们都摘掉吧,包起月亮,拆掉太阳,倒掉大海,扫清森林,因为现在一切没有意义了。”奥登的遣词造句肆无忌惮,直言不讳的哀悼,语无伦次地呐喊着一切疯话。
我一直都在旅行,行走在诗的时光中,我遇见过叶芝、阿加莎、艾吕雅、艾米、洛威尔、卡西莫多,聆听着奥登哼着的蓝调,随着醉舟的兰波漂流,触摸着诗中一切的阳光与阴霾,透过一个个字母耳语着,灵魂与灵魂的互换,感受着他们的无奈看着疯狂的爱尔兰将朝圣者刺伤成诗。
从那些零碎的思想我找回了失去的一些东西。
留点诗意给自己,找回对世界的初恋。
——后记





